《复杂性与后现代主义:理解复杂系统》,〔南非〕西利亚斯著,曾国屏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4月版,21.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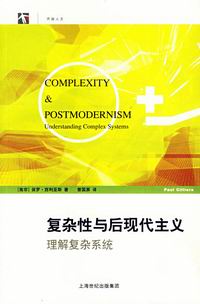 1996年,一个恶意的玩笑造成了一场世界级的学术地震。纽约
1996年,一个恶意的玩笑造成了一场世界级的学术地震。纽约
然而,同是1998年,一位南非科学哲学家保罗・西利亚斯(Paul Cilliers)也出版了一本书,(Complexity and Postmodernism? Understanding Complex Systems),书中充分肯定了后现代主义对于当今科学技术发展――不仅仅是某一分支研究――的巨大启示意义。在此先澄清两点:这位保罗可不是只会坐而论道的人文知识分子,此人在进入哲学圈以前,曾经长期从事利用神经网络进行计算机建模和模式识别的工作;且他所援引的后现代主义也并非《社会文本》那种文学路径的美国版,而是“正宗”的哲学路径的法国版,更准确地说,是以德里达、利奥塔尔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用他的话说:“后结构主义并非仅仅是一种话语分析的颠覆形式,它也是一种敏感于所论现象的复杂性的思维风格。”(第31页)
欲了解保罗的观点,先须了解何为“复杂”。“复杂”(complex)有别于“复合”(complicated),后者适用于喷气式飞机这样的系统,可以通过分析其组成部分获得关于系统的完整描述;而复杂系统则由于系统的各组成部分之间、系统与环境之间具有相互作用,不能使用这种先化整为零、再化零为整的分析方法。
“复杂”也有别于如今已成为大众流行词汇的“混沌”(chaos)。关于“混沌”的一个著名例子是所谓“蝴蝶效应”:一只蝴蝶扇一扇翅膀,就有可能在地球的另一端引发风暴,原因在于大气系统对于初始条件的敏感性。但保罗认为,混沌理论对复杂性研究的贡献是极其有限的,“在对复杂系统进行分析时,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并不是一个如此重要的问题。事实上,正是复杂系统的鲁棒(robust)本性,即其在不同条件下以同样的方式发生作用的能力,保证了系统的生存……自组织临界性(self-organised criticality)概念较之混沌的比喻更恰当。”(见本书前言)所谓“自组织”(self-organisation),指的是“复杂系统的一种能力,它使得系统可以自发地、适应性地发展或改变其内部结构,以更好地应付或处理它们的环境。”(第125页)所谓“自组织临界性”则是指,“许多合成的系统自然地向临界状态演化,其中微小的事件引发了能够对系统中任何数量的要素产生影响的链式反应……导致微小事件的机制同时也是导致重大事件的机制。”(第132页)――例如,一场街头口角引发了群体性的政治暴力,单个买家的投机行为令股票市场全盘崩溃。值得一提的是,在混沌理论家、比如国人熟悉的普里高津那里,上述临界状态又名“混沌的边缘”,被认为是依赖于某种有待混沌理论去发现的深层“原理”;保罗却支持复杂性科学家考夫曼的主张,认为自组织临界性可以通过“经济原理”加以解释,而不必依赖任何来自混沌理论的论据,盖因“复杂性”比“混沌”更具有普遍意义。
那么,哪些是具备自组织性质的复杂系统呢?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人类的语言,语言的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完全任意的,也不是完全可以预测的,而是一种“有理据的约定俗成”,因此,对语法结构可以做出充分的解释,但是只能做到不完全的预测――这一“有理据的约定俗成”即是语言的自组织性质。
保罗指出,语言研究存在两套相互对立的范式:一个是关注语言结构的乔姆斯基范式,运用生成规则的形式语法对语言进行描述;另一个是关注语言意义的索绪尔范式,将语言视为“能指―所指”的关系系统。不过,乔姆斯基范式符合图灵机的数学模型,因此很自然地构成了人工智能(AI)研究基础;而索绪尔范式虽然对人文学科影响甚巨,却因为缺少适用的数学模型,一向处于认知科学研究的视野之外。保罗则认为,“人们有可能利用神经网络理论对索绪尔的语言学提供数学模型,这等价于形式语法提供了对乔姆斯基语言学的数学描述。”(第43页)
有趣的是,在保罗看来,这一数学模型之所以有望实现,主要应归功于德里达对索绪尔的发展,也就是如今已成为大众流行词汇的“解构”。“解构”意味着将语言视为开放系统,而德里达创制的另一术语“延异”,则意味着将语言描述为一个有差异的系统。“德里达对语言的分析,对于我们讨论复杂性具有重要意义:它导致了‘归根结底把编码当作终极的规则系统的权威地位的终结’。总之,它反对基于规则的语言描述的可能性。”(第77页)“延异”其实对应于一种归复式的神经网络模型,“这种类型的网络具有许多的反馈环:某节点的输出可以成为该节点本身的输入,其间可以是通过其他节点,也可以是不通过其他节点。节点的活动因此不仅是由它和其他节点的差异所决定的,也是延迟到其本身的(以及其他的)活动反射回自身后决定的。在这种相互作用的复杂模式中,不可能说某种语符(或节点)表征了某种特定事物。”(第113页)这一神经网络模型可以很好地描述语言系统的自组织性质,亦即语言的“有理据的约定俗成”,而乔姆斯基范式和人工智能(AI)模型则或无视、或刻意弱化这一自组织性质。
说到底,对自组织性质的无视或刻意弱化,其实是西方思想主流的痼疾。诸如柏拉图的形式说、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笛卡儿的天赋说、洛克的初性说、休谟的单纯印象说、康德的感性和知性说、皮尔斯的科学理想状态说、胡塞尔的本质说、罗素的感觉材料说以及卡尔纳普的世界原子功能模块说等等,莫不具有两大特征:一是基础主义的知识论,二是还原论的分析方法,两者相辅相成。所谓基础主义的知识论,是指知识必须建立在必然、客观、永恒的“基础”之上,且能从这一“基础”中推导出来;所谓还原论的分析方法,是指所有自然现象都为一组能够明晰化的定律或规律所支配,因此总是可以将一个系统“还原”成其基本组成部分的集合。在这两项特征的影响下,“为了处理常常是极其大量的观察和实验数据,科学传统上极其强调的是遵循正确的方法。实验被设计出来控制大量的变量,并限制结果的可能解释。尽管这种步骤通常是不可避免的,但它意味着一些可能的结果被先验地消除了。选择一种方法就是一种预先腾空,以指向特定的一组解。遵循严格的方法,一定会提供绝妙的结果,但是经常导致没有充分重视对于方法的选取,而且还导致了使用一般术语来解释实验结果,而不是在合适的方法框架之中来解释。”(第32页)“科学的作用,传统上一直被理解为必须将知识固定在永久的网格上……如果人们不可能向网格上添加新东西,那就成了不够格的多余的一员。这种‘扔掉’策略,其结果是使得知识主干有资格作为‘科学的’部分越来越瘦弱。所有过于复杂的或包含着不确定性或不可预见性的事物,至少在暂时都要被搁置一旁。结果是,总体的人类知识的大部分,被轻视成不科学的……以这种狭窄的关于科学是什么的理解来工作,使得甚至生命科学(生物学)以及经验科学(工程学)都成为可疑的。”(第163~164页)
理所当然的,传统科学的“正确方法”在处理复杂系统的自组织性质时可谓束手无策。首先,自组织性质是反对基础主义的,“自组织的动力学本性,是不可能求助于某一个起源或某个永恒的原理来加以解释的,在此系统的结构由于偶发的、外部的因素以及历史的、内部的因素的相互作用而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事实上,自组织提供了这样的机制,藉此复杂结构可以进化,而无需假定第一开端或超验干预。”(第145~146页)其次,自组织性质也是反还原论的,“作为相互作用的复杂模式的结果,系统的行为不可能只按照它的原子论组分来解释……复杂的特征是通过系统中的相互作用而‘涌现’出来的。”(第146页)因此,若要对复杂系统提供适当的描述,关键不在于寻找某些可以充当万能钥匙的“深层原理”,而在于探询各种动态的、相互作用的“模式”。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对复杂系统的适当描述,将“不可能还原成简单的、连贯的并普遍有效的话语。”(第180页)这与人们对科学知识的惯常理解大相径庭,毕竟,“科学知识的习惯是诉诸连贯的元话语来使自己合法化的,元话语起着某种一般性统一的功能。如能找到这样一种元话语,便可能将所有形式的知识都结合成一个宏大叙事。”(第157页)而后现代主义恰恰来自对“元话语”的怀疑。保罗援引利奥塔尔的观点,拒绝“将科学解释为代表所有真知识的总体”,提倡“叙事地理解知识,将其描绘成多元性的较小故事”,使知识“在其使用的特定语境中很好地发挥作用。”――换言之,就是要增强“对于差异的敏感性”、以及“对不可通约的宽容”。这与费耶阿本德主张的科学的“无政府主义”实乃灵犀相通。
事实上,对科学知识的“叙事”理解,已经重新绘制了当今科学技术发展的版图。利奥塔尔1984年撰写《后现代状况》时的预言――“学科的思辨等级性,让位给了固有的……探索领域的‘扁平’网络,相应的前沿也处于不断地流动之中。”(第179页)――已经随着生物技术、遗传计算算法、计算机网络和虚拟现实等交叉学科的涌现而成为现实。至于前文提到的量子物理学家索卡尔,此公在攻击后现代知识界对科学的“胡说”之余,是否也不妨了解一些后现代主义的“正说”,免得自己像堂吉诃德一样,和风车作战?
 《从黑格尔到尼采:19世纪思维中的革命性决裂》,〔德〕洛维特著,李秋零译,三联书店出版社2006年4月版,27.00元
《从黑格尔到尼采:19世纪思维中的革命性决裂》,〔德〕洛维特著,李秋零译,三联书店出版社2006年4月版,27.00元
所谓“19世纪思维中的革命性决裂”,可以归结为作者的下述断语:“歌德的自然赖以为生的中点,黑格尔的精神在其中运动的调和,都在马克思和基尔克果那里重新分裂为外在性和内在性这两极,直到最后尼采要借助一次新的开始,从现代性的虚无中召回古代,并在从事这种试验时消逝在癫狂的黑暗之中。”本书内容博洽,材料翔尽,析理入微,但原创性不如作者的另一部思想史著作《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
《德国的历史观》,〔美〕伊格尔斯著,彭刚、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2月版,29.50元
 中国有句古谚:“其父报仇,其子杀人。”二十世纪纳粹主义的勃兴,其根源实已蕴含在十九世纪初的那一代德国人为报拿破仑侵略战争之仇而创立的各种政治体制和思想流派之中。由兰克和洪堡奠基的德国历史主义,便是把民族国家本身视为道德原则,宣称“当国家追求自己的更高利益――通常用权力政治的术语加以解释――时,它并不是有罪的,因为通过追求这些利益,它促进了更高的道德目的。”(第7页)这一历史主义所标举的“德国的历史观”,作为“西方的自然法学说”的对立面,思想上固然不能等同于纳粹主义,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无疑为后者上台扫清了道路。
中国有句古谚:“其父报仇,其子杀人。”二十世纪纳粹主义的勃兴,其根源实已蕴含在十九世纪初的那一代德国人为报拿破仑侵略战争之仇而创立的各种政治体制和思想流派之中。由兰克和洪堡奠基的德国历史主义,便是把民族国家本身视为道德原则,宣称“当国家追求自己的更高利益――通常用权力政治的术语加以解释――时,它并不是有罪的,因为通过追求这些利益,它促进了更高的道德目的。”(第7页)这一历史主义所标举的“德国的历史观”,作为“西方的自然法学说”的对立面,思想上固然不能等同于纳粹主义,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无疑为后者上台扫清了道路。
 《政治实践与公共空间:阿伦特的政治思想》,蔡英文著,新星出版社2006年3月版,28.00元
《政治实践与公共空间:阿伦特的政治思想》,蔡英文著,新星出版社2006年3月版,28.00元
本书是中文世界里第一本系统阐释阿伦特政治思想的专著,既然如此,其论述之有欠周到缜密也就颇值得谅解了。对于那些厌倦了各种自由主义论调、又对保守主义心存疑虑的读者来说,阿伦特的“公共领域”和“公民权力”理论,或许是一针强心剂。不过,阿伦特的政治思想有其鲜明的个性色彩,若以“体大思精”的标准衡量,似乎仍有逊色。
《虚己以游世:〈庄子〉哲学研究》,韩林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28.00元
现代的《庄子》研究一般是将内篇、外篇和杂篇区别对待,作者却对《庄子》中除了《说剑》篇以外的所有内容给出了前后一贯的哲学阐释,不可不谓勇于自信。此前他曾在一篇英文文章中“以同一个解释框架来解释维特根斯坦和庄子哲学”,而本书的主旨亦是“按照作者自己先行确立的解释框架给予《庄子》一书以一系统的哲学解释,但是同时又力图将这种解释建立在对文本的全面、系统、严谨的注释和分析基础之上。”――这既是阅读本书的好理由,也是不读它的好理由。
